桐庐越剧人生:唱一曲似水流年
时间:2025-01-13 17:02:16 阅读: 次 作者:一大碗 凉水淤泥
在谢群英的脑中,一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米上下的小个子,就躲在走廊的立柱之间,试图让柱子挡住小小身影,好叫老师看不见她。9到12岁的三年时光里,几乎每天,她都要在这条走廊里翻几十个跟斗。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带给她深深的恐惧,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她又充满感怀,儿时严格训练打下的坚实基本功,让她一生受益。这条走廊,就在桐庐中学艺术培训班的练功房外。
 1972年,桐庐中学请了几位外省的资深京昆演员,在各个村镇招生,收了49个学生,男女各半,开办了艺术培训班。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这是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三年后艺训班解散,孩子们各回各家,念书的念书,下地的下地。当时没有人知道,从这个班里走出来的很多人,未来会成为桐庐越剧圈的中流砥柱,甚至哺育出多位梅花奖名家演员,开启桐庐越剧的光辉年代。
1972年,桐庐中学请了几位外省的资深京昆演员,在各个村镇招生,收了49个学生,男女各半,开办了艺术培训班。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这是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三年后艺训班解散,孩子们各回各家,念书的念书,下地的下地。当时没有人知道,从这个班里走出来的很多人,未来会成为桐庐越剧圈的中流砥柱,甚至哺育出多位梅花奖名家演员,开启桐庐越剧的光辉年代。
桐庐越剧“黄埔军校”
考入艺训班时,谢群英只有9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只是喜欢唱唱跳跳,根本连艺训班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遑论学戏了。想不到,面试时的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竟会决定她此后大半生的道路,将她送上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领奖台。
她的同学里,有很多日后一生的同僚和朋友,其中也包括同样获得了梅花奖的王派传人单仰萍、范派传人陈雪萍。进了艺训班,除了语文数学课,其他时间都在学戏,主要学京剧,听的全是八个样板戏。从基本功开始练起,那是最苦的日子。她现在还能想起老师松开保护的手,让她自己来一次时的恐惧。这种恐惧并没有因为功力加深而减少,反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懂事而加深。
家长们先憋不住了。有一回,老师让谢群英站在桌子上翻前桥,她不敢,老师威吓道,不翻就不用吃中饭了。父母得知后,把她的日用品一应带回家来。可是当晚,女儿就偷偷跑回艺训班了。问及谢群英时,她却坚称,自己当时压根儿不喜欢唱戏,只是迷迷糊糊,就唱了一辈子。
陈雪萍的父亲倒是成功了。据说他看到食堂窗口柜台高过年幼女儿的头顶,小女孩努力举起饭碗伸进窗口的样子,做父亲的心疼不已,生怕女儿吃不饱饭,当即决定领回家继续读书。不料兜兜转转几年后,陈雪萍还是考进桐庐越剧团,成为越剧演员,已是后话。
“我们那一批打的是京昆的基础,出来功底都很好。”然而三年后艺训班毕业,却没有出路。“当时县里已经有一个文工团了,没有多余经费,我们只能原地解散,回去念书学习也不太跟得上。”好在一年后,事情有了转机。
百废待兴
1976年,桐庐恢复越剧团,谢群英是第一批考进剧团的演员。
桐庐越剧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桐庐民艺剧团。当时的团长倪雪芳来自嵊州,年方三十已是“出红台”十四年的老戏骨,二十岁就在桐庐的戏馆里挂牌。
桐庐越剧最早来自嵊县的唱书《呤哦调》,传入桐庐后,当地出现亦农亦艺的文书班。据《桐庐县志》记载,城乡有元宵、春社、秋社演剧之举,尤以县城“芦茨戏” 为甚。战争年代,唱戏人如倪雪芳,只能串村走坊,流浪唱戏。直到抗战后,下南乡“之江舞台”、四管乡“雅溪舞台”、凤川“新民舞台”、 窄溪“桐江舞台”、 深澳“大新舞台”......桐庐各地涌现一波民间戏班。
1950年9月4日,以原“云升舞台” 为基础,吸收闲散艺人,组成民艺剧团。那时剧团团员没有工钱,所有戏票收入都用在了装灯、搭台、开戏馆上。有时化妆油彩买不起,演员下了戏也不卸妆,用纱布盖在脸上睡觉,第二天接着演出,最长一次,六天六夜没有卸妆,以至于擦破脸都卸不下油彩。
在团员们的执着下,成立的十六年间,剧团逐渐有了自己的舞台和戏迷,人人都知道倪雪芳,走上10公里泥路,也要去听她唱戏。直到1966年,几经易变的剧团在文革期间彻底停止演出,越剧也成了不可说的话题。
待到十年后剧团重启,已是另一幅光景。越剧市场百废待兴,剧团演员男男女女都有,大部分和谢群英一样,艺训班京剧生出身,看样板戏长大,很少有人了解越剧。这成了剧团的第一件事,让大家认识越剧、喜爱越剧。
好在,越剧一直是极富创新力的剧种,百年前就借由当时的新媒体手段“电影”一举在大众范围里获得极大传播。“《碧玉簪》《红楼梦》《梁祝》......刚刚解禁那会儿都是连夜排队买票看的电影。”谢群英还记得第一次看越剧电影《碧玉簪》时的新奇和喜爱,对戏中的花旦名家金采风更是几近痴迷。以至于后来见到真人甚至拜师学艺,都仿佛银幕里的人跳出来,恍如梦境。
尽管观感不错,但要从原本的京剧转向越剧,并非易事。一开始,越剧念白,她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只能站在舞台旁一个人摸索,一边看台上人演戏,一边跟着念,从小角色开始慢慢入戏。
恢复女小生
你知道凌晨三点的桐庐是什么样子吗?
1979年的某一个凌晨,桐庐越剧团团长徐智灵听到,隔壁大礼堂里传来窸窸窣窣奇怪的声响,此时刚过凌晨两点,他战战兢兢打着手电,大着胆子到跑去一看,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居然在摸黑压腿练功。正是团里刚刚转练女小生的陈雪萍和周咏歌。
1978年,陈雪萍中学毕业,凭借过人天资考进了桐庐越剧院。起初父母对女儿又要去唱戏的态度不冷不热。恰逢政策改革,剧团学员每月工资22块5,要知道担任代课教师的陈母也只有14块,十多岁的小姑娘第一次感到越剧演员的荣光。
剧团生活很纯粹,早上六点起来跑步,跑完四公里回来压腿,练到七点吃早饭,八点多就开始上课了。学艺的孩子读书少,拍电影的时候,小演员们常有空闲,团长就会安排大家上文化课学习,读诗词文章、练字,甚至普及一些法律知识,有次讲什么叫正当防卫,陈雪萍印象极深。每次随团出门,团里都会带一个大纸箱,回来时装满《山海经》《读者文摘》等等杂志书籍,鼓励大家多多读书。在这样浓郁的文艺氛围下,团员们热衷探讨戏里的情节,写下对人物的心得体会。
刚开始随团巡演,小演员们至多跑跑龙套,不练功时陈雪萍就跑出去买零食,巡演三个月回来胖了十几斤,脸都圆鼓鼓的。
当时的团长徐智灵是嵊州人,一口嵊州话,“侬个则脸盘子,比屁股歪要大咧,还演花旦,不好演嘞!”话虽是调侃,意思却是当真。那会儿正是各个越剧团逐渐恢复女班的风潮,团里请来一位福建女小生老师,开始让陈雪萍跟着她学习,白天练功,晚上看团里演出。
陈雪萍这时候15岁上下,再练基本功其实蛮难的,但她性子犟,不喜欢落在人后。同她一起学小生的,还有周咏歌,两人时常暗暗较劲。一听老师表扬周咏歌早上六点练功,陈雪萍就不服气,给自己买了小闹铃,第二天五点半起床练功。没想到周咏歌第三天五点就起来了,接下去几天,四点半、四点、三点半、三点......直到后来,团长凌晨两点被吵醒,一束光照到黑暗舞台里的两个鬼影,好一顿教训。
很难讲是团长发掘了她的性格,让她走小生的戏路,还是演着演着,台上台下越来越像。面前的陈雪萍,性子里确有一些豪迈洒落的特质。“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说着说着,她自然地翘起二郎腿,像个爽利的假小子。
越剧电影的光辉岁月
1982年,桐庐越剧团彻底恢复全女班,一出大戏正在酝酿。一年后的浙江省首届戏剧节上,包朝赞编剧、桐庐越剧团排演的《春江月》正式演出,讲述平民绣花女的信义故事,冷不丁爆了,一举拿下优秀演出奖、优秀剧本奖。主要演员单仰萍、陈雪萍和谢群英等人风头一时无两。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春江月》在各地巡演叫好又叫座。“当时的桐庐县文化局党委书记郑锡纯,几乎跟着我们演出走,吃住都在团里,对越剧团相当重视,充满热情。”
1984年7月,剧团在上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甚至有黄牛倒卖戏票。台下既有普通观众,也有大师级名家,“十姐妹整整齐齐坐在台下看,结束后还来台上接见合影。”陈雪萍回忆起那个画面,仍是心潮澎湃。
其实早在彩排期间,金采风老师就曾受邀来到桐庐观摩。隔天,唱腔老师带着演员们拜访金老师住的酒店。那天的谢群英,就像追星少女,见到偶像般紧张激动,“过去不到一公里路,走得迷迷糊糊,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很久。”话也不会说,手也不知怎么摆了。只记得金老师很温和,夸奖了她一句“这个小鬼嗓子蛮灵的”。
直到在上海演出的这一次契机,才有了几人拜师的机缘。想来剧团早在写戏的阶段,就按照演员和角色适合的唱腔流派进行设计筹谋,也是希望演员们能与名师结缘,从而能有更高的艺术熏陶和突破。
那时剧场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基本休息。每年八月,徒儿们就会跑到上海,各找各师父练功学习。从桐庐到上海,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当时大巴要开六七个小时。往往是早晨七点赶汽车,一路慢慢摇,中午在嘉善停一停吃午饭。小姑娘一个人也不敢多逗留,生怕没等自己上车,车就出发了。到达上海,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范瑞娟老师当时住在长乐路,陈雪萍下了车按图索骥,等到师父家,天已经要黑了。陈雪萍每次带着戏去,练了哪段戏,唱给师父看,吃住都在师父家里,师父总是不厌其烦逐字点拨,还把自己绝版的戏曲磁带送给陈雪萍。师父不只授艺,还要教人。陈雪萍大大咧咧惯了,有一回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超短裤配上一双皮鞋,去了范老师家里,范老师就教育陈雪萍,“台上是男的,就一定是男的,但台下是女的,不能也把自己当男的。”2017年,范瑞娟老师仙逝,陈雪萍时常翻出旧时磁带,追忆起师父的叮咛教诲。直到自己成了前辈老师,曾经那些飘过耳边的话语,才有了踏实的意义。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春江月》翻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原班人马出演,在桐庐分水江畔的浪石埠和俞赵取景拍摄,并改名为《绣花女传奇》在全国上映。
尽管取自同一个故事,舞台表演和电影艺术还是截然不同。“电影还是遗憾的艺术,回看有些镜头,觉得还能更好,但是无法重来了。舞台不一样,每次表演一气呵成,同一出戏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第1遍演、第100遍演和第200遍演,可能演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春江月》大获成功后,桐庐越剧团乘胜追击。1985年秋排演的《桐江雨》,拿下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优秀演出、优秀剧本和优秀导演等在内的16个奖项。并于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成描写中国民间劳动妇女生活的哲理性正剧,改名为《桐花泪》,红遍大江南北。
自编自排,一口气产出两部口碑、票房双收的顶级作品,横扫戏剧节,并且接连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达成了一个常规县级剧团不可想象的里程碑,就连当时的杭州市委副书记杨招棣都盛赞,“一个小小的桐庐越剧团能拍两部电影,这是全国没有的,是罕见的。”
新征程
1987年,原本已经在筹拍的第三部桐庐越剧电影《月亮湖》因种种原因搁置,单仰萍跟随恩师王文娟调入上海红楼越剧团,不久后局里领导层也发生变更。
1992年,谢群英的女儿出生。剧团里新人辈出,表现也很不错,渐渐顶上她的角色。有一段时间,她也慢慢将生活重心放到了女儿身上,甚至不打算继续唱戏了。师父金采风别出苗头,“到我女儿十个月大的时候,我收到了师父的两度来信,劝我坚持自己的事业,不要轻易放弃。”
1994年,谢群英和陈雪萍一前一后调入杭州越剧团,其后分别在1998年的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2009年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上获得最高荣誉。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桐庐越剧团则显得有些落寞。
就在她们离开桐庐越剧团前夕,年仅15岁的王健刚刚从剧团艺训班被选拔进入越剧团。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个小花旦伴随剧团浮浮沉沉,如同一根台柱般坚守在桐庐越剧团的舞台上。
2000年,在老团长的引荐下,王健来到上海,拜访素未谋面的桐庐越剧团前辈单仰萍,那一年正是单仰萍获得第17届梅花奖的年份。近半个月时间,她住在单仰萍家中学习,还在单仰萍的陪同下,到王文娟老师家中进行辅导,对于一个精攻“王派”的花旦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激励。
2009年,王健成为剧团党支部书记,三年后越剧团改制为桐庐越剧传习中心和桐庐越剧演艺有限公司,王健一边作为演员享受舞台的演出,另一方面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管理剧团的行政工作,“我每个月最担心的就是剧团的工资能不能发……”更难之处在于人才培养,“年轻人总归向往更大的平台。”
尽管如此,在缺资金、缺人员的情况下,桐庐越剧团排演的《花溪情歌》获得满堂彩,在第十一届浙江省戏剧节上卷土重来,时隔多年拿下优秀表演奖,又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奖。
直到现在,除了谢群英、单仰萍和陈雪萍外,桐庐籍越剧演员里,还诞生了2002第19届梅花奖得主陈晓红和2004年第21届梅花奖得主王杭娟两位名家。小小的桐庐,已然培养出五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在全国县级市里,属于极为难得的。如何传承桐庐越剧的风采,持续培育出更多越剧演绎人才,这也成为桐庐越剧人长久的命题。从桐庐走出来的越剧名家们,也以此为己任。
就在去年底,桐庐提出创建越剧名家工作室。成立由五位梅花奖得主和优秀戏曲家任导师的“越剧名家工作室”,聘请谢群英、陈晓红、陈雪萍、王杭娟等艺术大师为工作室导师。未来,桐庐越剧传习中心也在筹谋,重新开办越剧团艺术培训班,自行培养年轻世代的越剧人才。

桐庐越剧“黄埔军校”
考入艺训班时,谢群英只有9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只是喜欢唱唱跳跳,根本连艺训班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遑论学戏了。想不到,面试时的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竟会决定她此后大半生的道路,将她送上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领奖台。
她的同学里,有很多日后一生的同僚和朋友,其中也包括同样获得了梅花奖的王派传人单仰萍、范派传人陈雪萍。进了艺训班,除了语文数学课,其他时间都在学戏,主要学京剧,听的全是八个样板戏。从基本功开始练起,那是最苦的日子。她现在还能想起老师松开保护的手,让她自己来一次时的恐惧。这种恐惧并没有因为功力加深而减少,反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懂事而加深。
家长们先憋不住了。有一回,老师让谢群英站在桌子上翻前桥,她不敢,老师威吓道,不翻就不用吃中饭了。父母得知后,把她的日用品一应带回家来。可是当晚,女儿就偷偷跑回艺训班了。问及谢群英时,她却坚称,自己当时压根儿不喜欢唱戏,只是迷迷糊糊,就唱了一辈子。
陈雪萍的父亲倒是成功了。据说他看到食堂窗口柜台高过年幼女儿的头顶,小女孩努力举起饭碗伸进窗口的样子,做父亲的心疼不已,生怕女儿吃不饱饭,当即决定领回家继续读书。不料兜兜转转几年后,陈雪萍还是考进桐庐越剧团,成为越剧演员,已是后话。
“我们那一批打的是京昆的基础,出来功底都很好。”然而三年后艺训班毕业,却没有出路。“当时县里已经有一个文工团了,没有多余经费,我们只能原地解散,回去念书学习也不太跟得上。”好在一年后,事情有了转机。
百废待兴
1976年,桐庐恢复越剧团,谢群英是第一批考进剧团的演员。
桐庐越剧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桐庐民艺剧团。当时的团长倪雪芳来自嵊州,年方三十已是“出红台”十四年的老戏骨,二十岁就在桐庐的戏馆里挂牌。
桐庐越剧最早来自嵊县的唱书《呤哦调》,传入桐庐后,当地出现亦农亦艺的文书班。据《桐庐县志》记载,城乡有元宵、春社、秋社演剧之举,尤以县城“芦茨戏” 为甚。战争年代,唱戏人如倪雪芳,只能串村走坊,流浪唱戏。直到抗战后,下南乡“之江舞台”、四管乡“雅溪舞台”、凤川“新民舞台”、 窄溪“桐江舞台”、 深澳“大新舞台”......桐庐各地涌现一波民间戏班。
1950年9月4日,以原“云升舞台” 为基础,吸收闲散艺人,组成民艺剧团。那时剧团团员没有工钱,所有戏票收入都用在了装灯、搭台、开戏馆上。有时化妆油彩买不起,演员下了戏也不卸妆,用纱布盖在脸上睡觉,第二天接着演出,最长一次,六天六夜没有卸妆,以至于擦破脸都卸不下油彩。
在团员们的执着下,成立的十六年间,剧团逐渐有了自己的舞台和戏迷,人人都知道倪雪芳,走上10公里泥路,也要去听她唱戏。直到1966年,几经易变的剧团在文革期间彻底停止演出,越剧也成了不可说的话题。
待到十年后剧团重启,已是另一幅光景。越剧市场百废待兴,剧团演员男男女女都有,大部分和谢群英一样,艺训班京剧生出身,看样板戏长大,很少有人了解越剧。这成了剧团的第一件事,让大家认识越剧、喜爱越剧。
好在,越剧一直是极富创新力的剧种,百年前就借由当时的新媒体手段“电影”一举在大众范围里获得极大传播。“《碧玉簪》《红楼梦》《梁祝》......刚刚解禁那会儿都是连夜排队买票看的电影。”谢群英还记得第一次看越剧电影《碧玉簪》时的新奇和喜爱,对戏中的花旦名家金采风更是几近痴迷。以至于后来见到真人甚至拜师学艺,都仿佛银幕里的人跳出来,恍如梦境。
尽管观感不错,但要从原本的京剧转向越剧,并非易事。一开始,越剧念白,她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只能站在舞台旁一个人摸索,一边看台上人演戏,一边跟着念,从小角色开始慢慢入戏。
恢复女小生
你知道凌晨三点的桐庐是什么样子吗?
1979年的某一个凌晨,桐庐越剧团团长徐智灵听到,隔壁大礼堂里传来窸窸窣窣奇怪的声响,此时刚过凌晨两点,他战战兢兢打着手电,大着胆子到跑去一看,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居然在摸黑压腿练功。正是团里刚刚转练女小生的陈雪萍和周咏歌。
1978年,陈雪萍中学毕业,凭借过人天资考进了桐庐越剧院。起初父母对女儿又要去唱戏的态度不冷不热。恰逢政策改革,剧团学员每月工资22块5,要知道担任代课教师的陈母也只有14块,十多岁的小姑娘第一次感到越剧演员的荣光。
剧团生活很纯粹,早上六点起来跑步,跑完四公里回来压腿,练到七点吃早饭,八点多就开始上课了。学艺的孩子读书少,拍电影的时候,小演员们常有空闲,团长就会安排大家上文化课学习,读诗词文章、练字,甚至普及一些法律知识,有次讲什么叫正当防卫,陈雪萍印象极深。每次随团出门,团里都会带一个大纸箱,回来时装满《山海经》《读者文摘》等等杂志书籍,鼓励大家多多读书。在这样浓郁的文艺氛围下,团员们热衷探讨戏里的情节,写下对人物的心得体会。
刚开始随团巡演,小演员们至多跑跑龙套,不练功时陈雪萍就跑出去买零食,巡演三个月回来胖了十几斤,脸都圆鼓鼓的。
当时的团长徐智灵是嵊州人,一口嵊州话,“侬个则脸盘子,比屁股歪要大咧,还演花旦,不好演嘞!”话虽是调侃,意思却是当真。那会儿正是各个越剧团逐渐恢复女班的风潮,团里请来一位福建女小生老师,开始让陈雪萍跟着她学习,白天练功,晚上看团里演出。
陈雪萍这时候15岁上下,再练基本功其实蛮难的,但她性子犟,不喜欢落在人后。同她一起学小生的,还有周咏歌,两人时常暗暗较劲。一听老师表扬周咏歌早上六点练功,陈雪萍就不服气,给自己买了小闹铃,第二天五点半起床练功。没想到周咏歌第三天五点就起来了,接下去几天,四点半、四点、三点半、三点......直到后来,团长凌晨两点被吵醒,一束光照到黑暗舞台里的两个鬼影,好一顿教训。
很难讲是团长发掘了她的性格,让她走小生的戏路,还是演着演着,台上台下越来越像。面前的陈雪萍,性子里确有一些豪迈洒落的特质。“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说着说着,她自然地翘起二郎腿,像个爽利的假小子。
越剧电影的光辉岁月
1982年,桐庐越剧团彻底恢复全女班,一出大戏正在酝酿。一年后的浙江省首届戏剧节上,包朝赞编剧、桐庐越剧团排演的《春江月》正式演出,讲述平民绣花女的信义故事,冷不丁爆了,一举拿下优秀演出奖、优秀剧本奖。主要演员单仰萍、陈雪萍和谢群英等人风头一时无两。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春江月》在各地巡演叫好又叫座。“当时的桐庐县文化局党委书记郑锡纯,几乎跟着我们演出走,吃住都在团里,对越剧团相当重视,充满热情。”
1984年7月,剧团在上海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甚至有黄牛倒卖戏票。台下既有普通观众,也有大师级名家,“十姐妹整整齐齐坐在台下看,结束后还来台上接见合影。”陈雪萍回忆起那个画面,仍是心潮澎湃。
其实早在彩排期间,金采风老师就曾受邀来到桐庐观摩。隔天,唱腔老师带着演员们拜访金老师住的酒店。那天的谢群英,就像追星少女,见到偶像般紧张激动,“过去不到一公里路,走得迷迷糊糊,感觉好像过了很久很久。”话也不会说,手也不知怎么摆了。只记得金老师很温和,夸奖了她一句“这个小鬼嗓子蛮灵的”。
直到在上海演出的这一次契机,才有了几人拜师的机缘。想来剧团早在写戏的阶段,就按照演员和角色适合的唱腔流派进行设计筹谋,也是希望演员们能与名师结缘,从而能有更高的艺术熏陶和突破。
那时剧场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基本休息。每年八月,徒儿们就会跑到上海,各找各师父练功学习。从桐庐到上海,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当时大巴要开六七个小时。往往是早晨七点赶汽车,一路慢慢摇,中午在嘉善停一停吃午饭。小姑娘一个人也不敢多逗留,生怕没等自己上车,车就出发了。到达上海,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范瑞娟老师当时住在长乐路,陈雪萍下了车按图索骥,等到师父家,天已经要黑了。陈雪萍每次带着戏去,练了哪段戏,唱给师父看,吃住都在师父家里,师父总是不厌其烦逐字点拨,还把自己绝版的戏曲磁带送给陈雪萍。师父不只授艺,还要教人。陈雪萍大大咧咧惯了,有一回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超短裤配上一双皮鞋,去了范老师家里,范老师就教育陈雪萍,“台上是男的,就一定是男的,但台下是女的,不能也把自己当男的。”2017年,范瑞娟老师仙逝,陈雪萍时常翻出旧时磁带,追忆起师父的叮咛教诲。直到自己成了前辈老师,曾经那些飘过耳边的话语,才有了踏实的意义。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春江月》翻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原班人马出演,在桐庐分水江畔的浪石埠和俞赵取景拍摄,并改名为《绣花女传奇》在全国上映。
尽管取自同一个故事,舞台表演和电影艺术还是截然不同。“电影还是遗憾的艺术,回看有些镜头,觉得还能更好,但是无法重来了。舞台不一样,每次表演一气呵成,同一出戏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第1遍演、第100遍演和第200遍演,可能演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春江月》大获成功后,桐庐越剧团乘胜追击。1985年秋排演的《桐江雨》,拿下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优秀演出、优秀剧本和优秀导演等在内的16个奖项。并于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成描写中国民间劳动妇女生活的哲理性正剧,改名为《桐花泪》,红遍大江南北。
自编自排,一口气产出两部口碑、票房双收的顶级作品,横扫戏剧节,并且接连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达成了一个常规县级剧团不可想象的里程碑,就连当时的杭州市委副书记杨招棣都盛赞,“一个小小的桐庐越剧团能拍两部电影,这是全国没有的,是罕见的。”
新征程
1987年,原本已经在筹拍的第三部桐庐越剧电影《月亮湖》因种种原因搁置,单仰萍跟随恩师王文娟调入上海红楼越剧团,不久后局里领导层也发生变更。
1992年,谢群英的女儿出生。剧团里新人辈出,表现也很不错,渐渐顶上她的角色。有一段时间,她也慢慢将生活重心放到了女儿身上,甚至不打算继续唱戏了。师父金采风别出苗头,“到我女儿十个月大的时候,我收到了师父的两度来信,劝我坚持自己的事业,不要轻易放弃。”
1994年,谢群英和陈雪萍一前一后调入杭州越剧团,其后分别在1998年的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2009年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上获得最高荣誉。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桐庐越剧团则显得有些落寞。
就在她们离开桐庐越剧团前夕,年仅15岁的王健刚刚从剧团艺训班被选拔进入越剧团。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个小花旦伴随剧团浮浮沉沉,如同一根台柱般坚守在桐庐越剧团的舞台上。
2000年,在老团长的引荐下,王健来到上海,拜访素未谋面的桐庐越剧团前辈单仰萍,那一年正是单仰萍获得第17届梅花奖的年份。近半个月时间,她住在单仰萍家中学习,还在单仰萍的陪同下,到王文娟老师家中进行辅导,对于一个精攻“王派”的花旦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激励。
2009年,王健成为剧团党支部书记,三年后越剧团改制为桐庐越剧传习中心和桐庐越剧演艺有限公司,王健一边作为演员享受舞台的演出,另一方面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管理剧团的行政工作,“我每个月最担心的就是剧团的工资能不能发……”更难之处在于人才培养,“年轻人总归向往更大的平台。”
尽管如此,在缺资金、缺人员的情况下,桐庐越剧团排演的《花溪情歌》获得满堂彩,在第十一届浙江省戏剧节上卷土重来,时隔多年拿下优秀表演奖,又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奖。
直到现在,除了谢群英、单仰萍和陈雪萍外,桐庐籍越剧演员里,还诞生了2002第19届梅花奖得主陈晓红和2004年第21届梅花奖得主王杭娟两位名家。小小的桐庐,已然培养出五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在全国县级市里,属于极为难得的。如何传承桐庐越剧的风采,持续培育出更多越剧演绎人才,这也成为桐庐越剧人长久的命题。从桐庐走出来的越剧名家们,也以此为己任。
就在去年底,桐庐提出创建越剧名家工作室。成立由五位梅花奖得主和优秀戏曲家任导师的“越剧名家工作室”,聘请谢群英、陈晓红、陈雪萍、王杭娟等艺术大师为工作室导师。未来,桐庐越剧传习中心也在筹谋,重新开办越剧团艺术培训班,自行培养年轻世代的越剧人才。
猜你喜欢
今年是范瑞娟先生的百年诞辰,为了缅怀范老师,绍兴小百花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用她给我们留下的范派艺术纪念她、缅怀她、想念她。...
由于越剧特别强调演员间的默契与配合,固定搭档通过长时间的合作,能够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表演风格。...
2024年,越剧界迎来了两位艺术大家的百年诞辰,一位是范派创始人范瑞娟先生,一位是著名剧作家顾锡东先生。...
越剧《孔雀东南飞》是范瑞娟、傅全香先生的代表作,2014年,为传承经典、致敬经典,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向上海越剧院学习了该剧目,由吴凤花、陈飞等主演,并于2021年4月亮相宁波逸夫剧院。...
明星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第八场山伯临终,陈雪萍主演。...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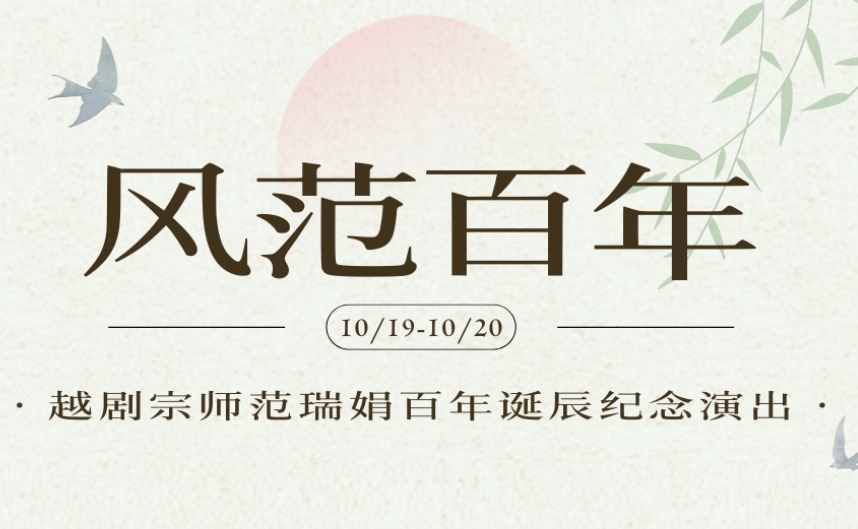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