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借鉴 再创辉煌——对二人台学习姐妹剧种之长的思考与建议
时间:2025-07-07 16:10:54 阅读: 次 作者:郜贵 荣杰
民歌《走西口》唱遍华夏大地,唱出国门,唱响世界,版本之多举世罕见。无论何种版本,无不激动人心,恋情绵绵,苦情凄凄,极强的感染力令听众或观众大动感情,甚至潸然落泪,泣不成声。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河北西北部地区、陕西东北部地区,鸡鸣四省,内涵颇丰。代表剧目《走西口》一出小戏,历史文化含量广博,观众喜闻乐见,百听不厌、百看不烦。
走西口纵贯清代中后期、近现代以至当代,乃中国历史上时间持续最长、涉及人数最多、留下足迹最远的陆地移民大潮。走西口大迁徙逐渐孕育出二人台这一剧种,特别是流行范围最广的内蒙古二人台,走西口者大都身处其境,堪称西口绝唱! 内蒙古二人台是不折不扣的内蒙古地方戏曲之首,与晋冀陕二人台比较,虽属同种同源却又颇具个性,别有风韵,独树一帜。她在广泛运用晋陕冀等地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当地蒙古族民歌的成分较多,载歌载舞,悠扬粗犷,豪放动听。就产生发展的历史而言,口里称“打玩艺儿 ”等,口外称“蒙古曲儿”等。内蒙古二人台曾经有过蒙古语与汉语混合演唱的“风搅雪”,由浓郁的蒙古族风情逐渐与汉族元素融合,发展到学习戏曲表演,增加戏剧情节,登上戏剧舞台。目前,二人台语言中仍然有蒙古语言印迹,只是将本来的蒙古语拼音变为唱腔中的装饰音,二人台演唱中常用的装饰音“嘚嘞赛”便是原汁原味的蒙古语。可见,内蒙古二人台起初由蒙古语与汉语混合演唱,最终发展进化到运用汉语演唱,是蒙古民歌与汉民歌互融互和的产物。除内蒙古二人台之外,将两个民族的语言与民歌通过戏曲打磨成为一个独立剧种,在中国戏曲史上绝无仅有!
内蒙古二人台是不折不扣的内蒙古地方戏曲之首,与晋冀陕二人台比较,虽属同种同源却又颇具个性,别有风韵,独树一帜。她在广泛运用晋陕冀等地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当地蒙古族民歌的成分较多,载歌载舞,悠扬粗犷,豪放动听。就产生发展的历史而言,口里称“打玩艺儿 ”等,口外称“蒙古曲儿”等。内蒙古二人台曾经有过蒙古语与汉语混合演唱的“风搅雪”,由浓郁的蒙古族风情逐渐与汉族元素融合,发展到学习戏曲表演,增加戏剧情节,登上戏剧舞台。目前,二人台语言中仍然有蒙古语言印迹,只是将本来的蒙古语拼音变为唱腔中的装饰音,二人台演唱中常用的装饰音“嘚嘞赛”便是原汁原味的蒙古语。可见,内蒙古二人台起初由蒙古语与汉语混合演唱,最终发展进化到运用汉语演唱,是蒙古民歌与汉民歌互融互和的产物。除内蒙古二人台之外,将两个民族的语言与民歌通过戏曲打磨成为一个独立剧种,在中国戏曲史上绝无仅有!
我们开阔视野进行广泛类比,如流行于东北三省的二人转,产生于山东胶东半岛黄河入海口近处广饶县的吕剧,兴起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梅戏,她们从起源到演变都与二人台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类较小的剧种几乎全部发端于社会最底层,全部由多种民间小调相互交融而成,全部通过由“打坐腔”汲取大剧种的营养走上舞台,成为戏曲大花园中的鲜花,全部以农业甚至是茶业、牧业劳动者的劳作为底色,全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才由低俗向雅俗共赏发展,全部充满挚情淳朴的生活气息与芳香醉人的泥土气息,全部从演唱劳动者的朴实单纯感情逐渐向多元化的丰富感情拓展……
学习二人转易于国人接受的语言
语言艺术占有戏曲艺术的重要地位,地方戏剧若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定要学习运用国人基本能够接受的普通话。二人台要想冲破方言的限制越走越远,越唱越响,必须从全国大众化的语言表情达意上狠下功夫,否则只能让蒙晋冀陕交界处方言区的观众自我欣赏,限制了二人台扩展的空间。
我们知道,但凡流行二人台的地方全部流行晋剧中路梆子,晋剧中路梆子是二人台最亲密的姐妹艺术。而晋剧中路梆子的著名艺术家们早已开始向普通话学习,改造自己方言区以外观众难以听懂的俚语,创造国人基本都能接受的新型晋剧语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晋剧中路梆子黑头一角,民国初期便开始探索打造新型发音,且大获成功!以距北京较近的张家口、大同为试验田,刻意学习京剧花脸的唱法,科学性与创新性并举,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为天下戏曲人刮目相看。国粹京剧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产物,如果仍然以安徽方言唱白,拒不接受北京周边诸如评剧等剧种之长,乃至黄河流域梆子戏之优点,一定难以立足于清王朝的帝都北京。二人转正是以语言近乎普通话为优势,适当剔除方言俚语,才得以唱响全国,几乎为所有国人接受。
明末清初,以山东、河北为代表的居民闯关东,以山西、河北、陕西为代表的居民走西口。可以说走西口孕育了二人台,闯关东孕育了二人转,两个方向的大移民培育了两个极为相似的戏曲剧种。二人转、二人台共同拥有载歌载舞、打科插浑的特点,二人转的代表剧目《西厢》《蓝桥》《浔阳楼》《包公赔情》《开店》等具有中原传统戏曲的深深烙印;而二人台的代表剧目却并无中原传统剧目的真切影子,二人台因大量吸收蒙古歌舞而更具特色,因与蒙古族歌舞相融而开辟了一块崭新天地,诸如《走西口》《五哥放羊》《牧牛》《借冠子》《挂红灯》等戏生活气息浓郁,情真意切,独具情韵。《走西口》虽为一折二人台小戏,但历史文化含量颇丰,令人联想到长达三四百年汉族百姓向蒙古高原大移民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断之场景,诱人沉思,催人落泪……
追溯历史,二人转的基础语言东北方言与北京方言有密切关系,二人转的方言近乎北京及周边的冀鲁方言,仅从发音上略微修正便可变作国人基本都能够听懂的普通话。蒙晋冀陕交界处的方言虽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晋方言系,但据有关专家深入研究发现,其中距今比较久远的元朝遗留方言较多。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区方言,因吸收了部分蒙古语词汇,更让与普通话差距不太大的中原乃至部分北方人亦难以听懂。
二人台首戏《走西口》中男主角泰春第一句唱词为:“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年限”一词便方言性特强,即使北方其他小方言区的人也难解其意。
又如传统二人台代表剧《卖碗》中主角王成刚一出场的这句唱词:“阳婆婆出来一杆杆高,王成我卖碗走一遭。”内蒙古地区距北京最近的赤峰人恐怕听“阳婆婆”与“走一遭”都会一头雾水。
总之,东北二人转仅最基本的普通话语言优势就极大,为二人转走向全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历史文化含量特别丰富的二人台应学习运用普通话,为今后的发展以及发扬光大做好基础。
学习吕剧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曾经以小戏《李二嫂改嫁》一度令国人瞩目的吕剧,起源于黄河入海口近处的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可谓与二人台“同饮黄河水”。《李二嫂改嫁》一炮打响全国,令人见识到中华戏曲大家庭中有一位稚嫩而美丽的少女,清新别致。吕剧从业者向来孜孜以求、自强不息,坚持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他们探索精神十足,坚持不懈改革创新,执着追求难能可贵。他们善于学习其他剧种之长,探索不止,突飞猛进,一鼓作气排演新戏,先后将《苦菜花》《乡人俚语》《军嫂》《潮涌黄河口》等大量优秀剧目奉献出来,为观众喜闻乐见,令同行刮目相看。使吕剧在地方小戏颇多的山东省脱颖而出,盛名远扬,很快成为山东省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全国八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仅数十年时光,吕剧便从胶东半岛快速跃进,向四面八方辐射,将种子播撒向江苏、河北、辽宁、吉林、新疆、黑龙江的戏曲沃土,使吕剧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然而,二人台在向外扩展方面相形见绌,裹足不前,多少年内仅徘徊于蒙晋冀陕交界地区。
吕剧的历史只不过百年有余,而二人台的经历虽曲曲折折却已跌跌撞撞行进了二百年左右。显而易见,将吕剧视为涉世未深的小妹妹,将二人台视为成熟端庄的大姐姐理所当然。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不得不承认,二人台的知名度难以与吕剧相比。
二人台、吕剧的诞生与初期的成长具有特别相似之处,最初都出自社会最底层之口,都由民间小调逐步演绎而成,都因倾诉社会底层的疾苦而为广大劳苦大众青睐,当初都是不折不扣的“下里巴人”……然而,发展壮大的速度快慢却异常显明,仿佛是一个骑马一个徒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且稚嫩的吕剧快速向外传播,年富力强的二人台却常常囿于“一方水土”,很少“四处闯荡”;吕剧的语言定位是与普通话相近的山东官话,二人台的语言定位是地方方言俚语……二者同样移植过一些传统大戏,如吕剧的《哑女告状》《端平桥》《拾玉镯》等,二人台的《墙头记》《茶瓶记》等,但却没有一定的轰动效应,都没有为全国观众重视。
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言,吕剧同样是二人台稚嫩的小妹,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大不可喻。吕剧“第一戏”《王小赶脚》剧情为:一位小媳妇雇脚骑驴回娘家,与赶毛驴的小男孩一路上说笑逗乐……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虽起初为小戏一折,却能北跨滔滔黄河、巍巍长城,添枝加叶扩展为一出联结晋北农村与内蒙古的大戏。传统的《走西口》戏虽小,却情感丰富,内涵多元,堪称戏曲以小见大的典范。
由此可见,二人台的久远历史与先天条件远超越吕剧。吕剧的勇于创新对于二人台开辟革新之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然,从首当其冲的语言体系而言,内蒙古因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基础方言特别复杂,难以形成自己的官话。所以二人台应该研究实施一种既有地方特色又接近于普通话的语言确定为标准,打造一种适合向全国推广的崭新的“二人台语言”。
其次,应该广泛研究同类甚至是近亲姐妹艺术成功的先进经验,从中吸收养分,取其精华。吕剧善于从其他剧种取长补短的优点十分突出,该剧种演出的《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也是移植剧目,而戏曲表现方式的本土化异常巧妙,语言与曲调的齐鲁化令人叹为观止。吕剧中诸如《秦雪梅观鱼》《朱买臣休妻》等剧目,无不是向豫剧、评剧、山东梆子等大型剧种学习的产物,移植加工改造得很成功,看不出原剧种的痕迹。另外,勇于创新更是吕剧前进步伐快捷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创作公演的《石龙湾》《张王李赵》《滩回水转》《李二嫂后传》《浪子回头》等等,大都为观众喜闻乐见。吕剧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非常值得二人台反思自己,加倍努力,奋起直追。
这段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词传遍华夏,唱响世界,老中青甚至是少年几乎耳熟能详,以至信口唱出。相比而言,二人台的爱情戏《五哥放羊》《挂红灯》《走西口》等,虽浪漫不足,但生活气息浓郁,歌舞结合,只因语言限制且缺乏经典台词而有所逊色。黄梅戏如今作为江南的代表性剧种,虽历史跨度及孕育母体与二人台相似,产生因素与二人台相似,依赖的基础与二人台近似,然而,能够跻身于中国戏曲四大剧种,实实在在难能可贵!
二人台诞生之初便流行于蒙晋冀陕四省交界的辽阔区域,黄梅戏却仅徘徊于鄂皖赣交界处的大山之中;二人台不但吸收了晋北、冀西北、陕北的汉语民歌,而且还有蒙古族歌舞的天然基因,黄梅戏却起初仅有吸收鄂皖交界处民歌的条件,少有南方少数民族歌舞的印记;二人台骨子里有载歌载舞的优势,也有吸收邻近大剧种的尝试;黄梅戏却基本上仅具有民歌风格,仅注重戏曲表演,舞蹈方面有所欠缺;二人台传统剧目大都现实生活基础扎实,黄梅戏传统剧目却侧重于古典的神话浪漫……列举多种因素,不难发现二人台发展壮大的先天条件大都比黄梅戏优越,但二人台发展的速度却比较缓慢。时至今日,我们确实要取黄梅戏之长,补二人台之短!
追溯黄梅戏的起源及发展壮大,语言大众化的传播成为重中之重。二人台流传的大方言区属晋方言区,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晋方言区的东北边距京方言区仅有二三百里之遥,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堪称近邻!黄梅戏最初兴起于皖鄂赣交界处的特殊小方言区内,属于发音特别的江南语系。语调一般难懂,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梅戏从业者紧跟时代步伐,将自己的标准语言基本确定为中原南端的江淮方言。如今,黄梅戏的唱白虽有鄂皖赣方言的烙印,却成为全国观众普遍可以接受的黄梅戏“普通话”,创意可佳!反观二人台,其语调、方言则没有被全国广大观众接受。
黄梅戏的起源与形成几乎等同于二人台,由“打坐腔”的民间小调,逐步演进为登上舞台表演的民间小戏。她自始至终没有忘本,牢牢掌握以小见大、以小胜大的理念,正因为黄梅戏从业者不忘小戏之“初心”,精心打造自己的语言,积极向普通话靠拢,才使自己发展速度惊人,誉满全国,走向世界。也培养出众多全国名声显赫、如雷贯耳的大家。
黄梅戏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二人台从业者认真学习,由表及里深刻认识二人台的灵魂与精神,为二人台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崭新思路,开辟可行道路……
继续学习蒙古族歌舞之长
二人台与二人转、吕剧等小剧种一样,大都从民间歌舞发展演变而来。二人台却因与生俱来有游牧民歌的基因,自然天成,风韵独特,具有农牧文化的印记,草原生活的记忆,原始的自然美难能可贵,个性鲜明,别具情韵。诸如《五哥放羊》《牧牛》《海莲花》《阿拉腾奔花》《吉德森玛》等二人台小戏,剧名就有蒙古地域特色。
晋陕冀汉族民歌与蒙古族民歌融合为二人台,载歌载舞是二人台的特色,现如今随着蒙古族舞蹈的创新发展,二人台应学习蒙古族歌舞与时俱进的形式与精神,保持二人台的独特魅力。
只有纵向深刻探究真实的历史,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我;只有横向广泛比较类似的事物,才能更确切地发现自我的不足。将二人台放置于中国戏曲的广阔天地,与产生及历史发展近似的黄梅戏、吕剧、二人转等剧种进行多方面、多元素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二人台的历史及现状。二人台当然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优势,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深刻反思,改革创新。
首先,组建一支专门研究二人台语言的团队,细心琢磨,潜心推敲,兼收并蓄。定性一种既接近普通话又不失地方特色的“新型二人台语言体系”。
其次,发扬大戏小做、以小见大、表小里大的固有特色,将二人台雕琢成为小巧玲珑的精致艺术品。将看似无戏实则有戏、看似小戏实则大戏———诸如《走西口》具有的传统优势打造得更加引人注目,令观众喜爱。
再次,从当地的民风民俗出发,继续发扬二人台骨子里淳朴而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特点;继续发挥固有的特色,让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更加有机结合;注入当代文化因素,扩展二人台观众群体。
第四,发扬二人台与生俱来的长处,继续汲取蒙古族歌舞的营养,找准切入点,巧妙对接,以体现自己独具一格的本色及魅力。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市花为丁香花,我们应该将二人台培育成具有丁香品格的剧种,花朵虽小不算艳丽,却繁花似锦、芳香诱人、独具风姿、历史悠久,令人喜爱。
这是笔者对二人台艺术发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作者简介】
郜贵,内蒙古作协会员;荣杰,就职于呼和浩特市非遗研究院戏研室
走西口纵贯清代中后期、近现代以至当代,乃中国历史上时间持续最长、涉及人数最多、留下足迹最远的陆地移民大潮。走西口大迁徙逐渐孕育出二人台这一剧种,特别是流行范围最广的内蒙古二人台,走西口者大都身处其境,堪称西口绝唱!

我们开阔视野进行广泛类比,如流行于东北三省的二人转,产生于山东胶东半岛黄河入海口近处广饶县的吕剧,兴起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梅戏,她们从起源到演变都与二人台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类较小的剧种几乎全部发端于社会最底层,全部由多种民间小调相互交融而成,全部通过由“打坐腔”汲取大剧种的营养走上舞台,成为戏曲大花园中的鲜花,全部以农业甚至是茶业、牧业劳动者的劳作为底色,全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才由低俗向雅俗共赏发展,全部充满挚情淳朴的生活气息与芳香醉人的泥土气息,全部从演唱劳动者的朴实单纯感情逐渐向多元化的丰富感情拓展……
学习二人转易于国人接受的语言
语言艺术占有戏曲艺术的重要地位,地方戏剧若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定要学习运用国人基本能够接受的普通话。二人台要想冲破方言的限制越走越远,越唱越响,必须从全国大众化的语言表情达意上狠下功夫,否则只能让蒙晋冀陕交界处方言区的观众自我欣赏,限制了二人台扩展的空间。
我们知道,但凡流行二人台的地方全部流行晋剧中路梆子,晋剧中路梆子是二人台最亲密的姐妹艺术。而晋剧中路梆子的著名艺术家们早已开始向普通话学习,改造自己方言区以外观众难以听懂的俚语,创造国人基本都能接受的新型晋剧语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晋剧中路梆子黑头一角,民国初期便开始探索打造新型发音,且大获成功!以距北京较近的张家口、大同为试验田,刻意学习京剧花脸的唱法,科学性与创新性并举,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为天下戏曲人刮目相看。国粹京剧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产物,如果仍然以安徽方言唱白,拒不接受北京周边诸如评剧等剧种之长,乃至黄河流域梆子戏之优点,一定难以立足于清王朝的帝都北京。二人转正是以语言近乎普通话为优势,适当剔除方言俚语,才得以唱响全国,几乎为所有国人接受。
明末清初,以山东、河北为代表的居民闯关东,以山西、河北、陕西为代表的居民走西口。可以说走西口孕育了二人台,闯关东孕育了二人转,两个方向的大移民培育了两个极为相似的戏曲剧种。二人转、二人台共同拥有载歌载舞、打科插浑的特点,二人转的代表剧目《西厢》《蓝桥》《浔阳楼》《包公赔情》《开店》等具有中原传统戏曲的深深烙印;而二人台的代表剧目却并无中原传统剧目的真切影子,二人台因大量吸收蒙古歌舞而更具特色,因与蒙古族歌舞相融而开辟了一块崭新天地,诸如《走西口》《五哥放羊》《牧牛》《借冠子》《挂红灯》等戏生活气息浓郁,情真意切,独具情韵。《走西口》虽为一折二人台小戏,但历史文化含量颇丰,令人联想到长达三四百年汉族百姓向蒙古高原大移民的浩浩荡荡、绵延不断之场景,诱人沉思,催人落泪……
追溯历史,二人转的基础语言东北方言与北京方言有密切关系,二人转的方言近乎北京及周边的冀鲁方言,仅从发音上略微修正便可变作国人基本都能够听懂的普通话。蒙晋冀陕交界处的方言虽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晋方言系,但据有关专家深入研究发现,其中距今比较久远的元朝遗留方言较多。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区方言,因吸收了部分蒙古语词汇,更让与普通话差距不太大的中原乃至部分北方人亦难以听懂。
二人台首戏《走西口》中男主角泰春第一句唱词为:“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年限”一词便方言性特强,即使北方其他小方言区的人也难解其意。
又如传统二人台代表剧《卖碗》中主角王成刚一出场的这句唱词:“阳婆婆出来一杆杆高,王成我卖碗走一遭。”内蒙古地区距北京最近的赤峰人恐怕听“阳婆婆”与“走一遭”都会一头雾水。
总之,东北二人转仅最基本的普通话语言优势就极大,为二人转走向全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历史文化含量特别丰富的二人台应学习运用普通话,为今后的发展以及发扬光大做好基础。
学习吕剧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曾经以小戏《李二嫂改嫁》一度令国人瞩目的吕剧,起源于黄河入海口近处的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可谓与二人台“同饮黄河水”。《李二嫂改嫁》一炮打响全国,令人见识到中华戏曲大家庭中有一位稚嫩而美丽的少女,清新别致。吕剧从业者向来孜孜以求、自强不息,坚持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他们探索精神十足,坚持不懈改革创新,执着追求难能可贵。他们善于学习其他剧种之长,探索不止,突飞猛进,一鼓作气排演新戏,先后将《苦菜花》《乡人俚语》《军嫂》《潮涌黄河口》等大量优秀剧目奉献出来,为观众喜闻乐见,令同行刮目相看。使吕剧在地方小戏颇多的山东省脱颖而出,盛名远扬,很快成为山东省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全国八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仅数十年时光,吕剧便从胶东半岛快速跃进,向四面八方辐射,将种子播撒向江苏、河北、辽宁、吉林、新疆、黑龙江的戏曲沃土,使吕剧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然而,二人台在向外扩展方面相形见绌,裹足不前,多少年内仅徘徊于蒙晋冀陕交界地区。
吕剧的历史只不过百年有余,而二人台的经历虽曲曲折折却已跌跌撞撞行进了二百年左右。显而易见,将吕剧视为涉世未深的小妹妹,将二人台视为成熟端庄的大姐姐理所当然。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不得不承认,二人台的知名度难以与吕剧相比。
二人台、吕剧的诞生与初期的成长具有特别相似之处,最初都出自社会最底层之口,都由民间小调逐步演绎而成,都因倾诉社会底层的疾苦而为广大劳苦大众青睐,当初都是不折不扣的“下里巴人”……然而,发展壮大的速度快慢却异常显明,仿佛是一个骑马一个徒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且稚嫩的吕剧快速向外传播,年富力强的二人台却常常囿于“一方水土”,很少“四处闯荡”;吕剧的语言定位是与普通话相近的山东官话,二人台的语言定位是地方方言俚语……二者同样移植过一些传统大戏,如吕剧的《哑女告状》《端平桥》《拾玉镯》等,二人台的《墙头记》《茶瓶记》等,但却没有一定的轰动效应,都没有为全国观众重视。
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言,吕剧同样是二人台稚嫩的小妹,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大不可喻。吕剧“第一戏”《王小赶脚》剧情为:一位小媳妇雇脚骑驴回娘家,与赶毛驴的小男孩一路上说笑逗乐……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虽起初为小戏一折,却能北跨滔滔黄河、巍巍长城,添枝加叶扩展为一出联结晋北农村与内蒙古的大戏。传统的《走西口》戏虽小,却情感丰富,内涵多元,堪称戏曲以小见大的典范。
由此可见,二人台的久远历史与先天条件远超越吕剧。吕剧的勇于创新对于二人台开辟革新之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然,从首当其冲的语言体系而言,内蒙古因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基础方言特别复杂,难以形成自己的官话。所以二人台应该研究实施一种既有地方特色又接近于普通话的语言确定为标准,打造一种适合向全国推广的崭新的“二人台语言”。
其次,应该广泛研究同类甚至是近亲姐妹艺术成功的先进经验,从中吸收养分,取其精华。吕剧善于从其他剧种取长补短的优点十分突出,该剧种演出的《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也是移植剧目,而戏曲表现方式的本土化异常巧妙,语言与曲调的齐鲁化令人叹为观止。吕剧中诸如《秦雪梅观鱼》《朱买臣休妻》等剧目,无不是向豫剧、评剧、山东梆子等大型剧种学习的产物,移植加工改造得很成功,看不出原剧种的痕迹。另外,勇于创新更是吕剧前进步伐快捷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创作公演的《石龙湾》《张王李赵》《滩回水转》《李二嫂后传》《浪子回头》等等,大都为观众喜闻乐见。吕剧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非常值得二人台反思自己,加倍努力,奋起直追。
这段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唱词传遍华夏,唱响世界,老中青甚至是少年几乎耳熟能详,以至信口唱出。相比而言,二人台的爱情戏《五哥放羊》《挂红灯》《走西口》等,虽浪漫不足,但生活气息浓郁,歌舞结合,只因语言限制且缺乏经典台词而有所逊色。黄梅戏如今作为江南的代表性剧种,虽历史跨度及孕育母体与二人台相似,产生因素与二人台相似,依赖的基础与二人台近似,然而,能够跻身于中国戏曲四大剧种,实实在在难能可贵!
二人台诞生之初便流行于蒙晋冀陕四省交界的辽阔区域,黄梅戏却仅徘徊于鄂皖赣交界处的大山之中;二人台不但吸收了晋北、冀西北、陕北的汉语民歌,而且还有蒙古族歌舞的天然基因,黄梅戏却起初仅有吸收鄂皖交界处民歌的条件,少有南方少数民族歌舞的印记;二人台骨子里有载歌载舞的优势,也有吸收邻近大剧种的尝试;黄梅戏却基本上仅具有民歌风格,仅注重戏曲表演,舞蹈方面有所欠缺;二人台传统剧目大都现实生活基础扎实,黄梅戏传统剧目却侧重于古典的神话浪漫……列举多种因素,不难发现二人台发展壮大的先天条件大都比黄梅戏优越,但二人台发展的速度却比较缓慢。时至今日,我们确实要取黄梅戏之长,补二人台之短!
追溯黄梅戏的起源及发展壮大,语言大众化的传播成为重中之重。二人台流传的大方言区属晋方言区,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晋方言区的东北边距京方言区仅有二三百里之遥,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堪称近邻!黄梅戏最初兴起于皖鄂赣交界处的特殊小方言区内,属于发音特别的江南语系。语调一般难懂,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梅戏从业者紧跟时代步伐,将自己的标准语言基本确定为中原南端的江淮方言。如今,黄梅戏的唱白虽有鄂皖赣方言的烙印,却成为全国观众普遍可以接受的黄梅戏“普通话”,创意可佳!反观二人台,其语调、方言则没有被全国广大观众接受。
黄梅戏的起源与形成几乎等同于二人台,由“打坐腔”的民间小调,逐步演进为登上舞台表演的民间小戏。她自始至终没有忘本,牢牢掌握以小见大、以小胜大的理念,正因为黄梅戏从业者不忘小戏之“初心”,精心打造自己的语言,积极向普通话靠拢,才使自己发展速度惊人,誉满全国,走向世界。也培养出众多全国名声显赫、如雷贯耳的大家。
黄梅戏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二人台从业者认真学习,由表及里深刻认识二人台的灵魂与精神,为二人台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崭新思路,开辟可行道路……
继续学习蒙古族歌舞之长
二人台与二人转、吕剧等小剧种一样,大都从民间歌舞发展演变而来。二人台却因与生俱来有游牧民歌的基因,自然天成,风韵独特,具有农牧文化的印记,草原生活的记忆,原始的自然美难能可贵,个性鲜明,别具情韵。诸如《五哥放羊》《牧牛》《海莲花》《阿拉腾奔花》《吉德森玛》等二人台小戏,剧名就有蒙古地域特色。
晋陕冀汉族民歌与蒙古族民歌融合为二人台,载歌载舞是二人台的特色,现如今随着蒙古族舞蹈的创新发展,二人台应学习蒙古族歌舞与时俱进的形式与精神,保持二人台的独特魅力。
只有纵向深刻探究真实的历史,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我;只有横向广泛比较类似的事物,才能更确切地发现自我的不足。将二人台放置于中国戏曲的广阔天地,与产生及历史发展近似的黄梅戏、吕剧、二人转等剧种进行多方面、多元素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二人台的历史及现状。二人台当然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优势,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深刻反思,改革创新。
首先,组建一支专门研究二人台语言的团队,细心琢磨,潜心推敲,兼收并蓄。定性一种既接近普通话又不失地方特色的“新型二人台语言体系”。
其次,发扬大戏小做、以小见大、表小里大的固有特色,将二人台雕琢成为小巧玲珑的精致艺术品。将看似无戏实则有戏、看似小戏实则大戏———诸如《走西口》具有的传统优势打造得更加引人注目,令观众喜爱。
再次,从当地的民风民俗出发,继续发扬二人台骨子里淳朴而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特点;继续发挥固有的特色,让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更加有机结合;注入当代文化因素,扩展二人台观众群体。
第四,发扬二人台与生俱来的长处,继续汲取蒙古族歌舞的营养,找准切入点,巧妙对接,以体现自己独具一格的本色及魅力。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市花为丁香花,我们应该将二人台培育成具有丁香品格的剧种,花朵虽小不算艳丽,却繁花似锦、芳香诱人、独具风姿、历史悠久,令人喜爱。
这是笔者对二人台艺术发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作者简介】
郜贵,内蒙古作协会员;荣杰,就职于呼和浩特市非遗研究院戏研室
猜你喜欢
8月28日在土右旗美岱召景区广场演出黄河情韵北疆和声开幕式文艺晚会,8月29日唱享二人台共筑北疆情惠民演出活动。...
一支专业剧团、200多支民间剧团、146家文化大院正在土右旗大地上传承、发展着二人台这项艺术,即将举办的第六届内蒙古二人台文化艺术节也会再一次将镜头聚焦土右旗、聚焦二人台,这个唱腔曲调悠扬高亢、音乐古拙、方言道白泼辣、剧情短小精悍极富生活气息的艺术形式。...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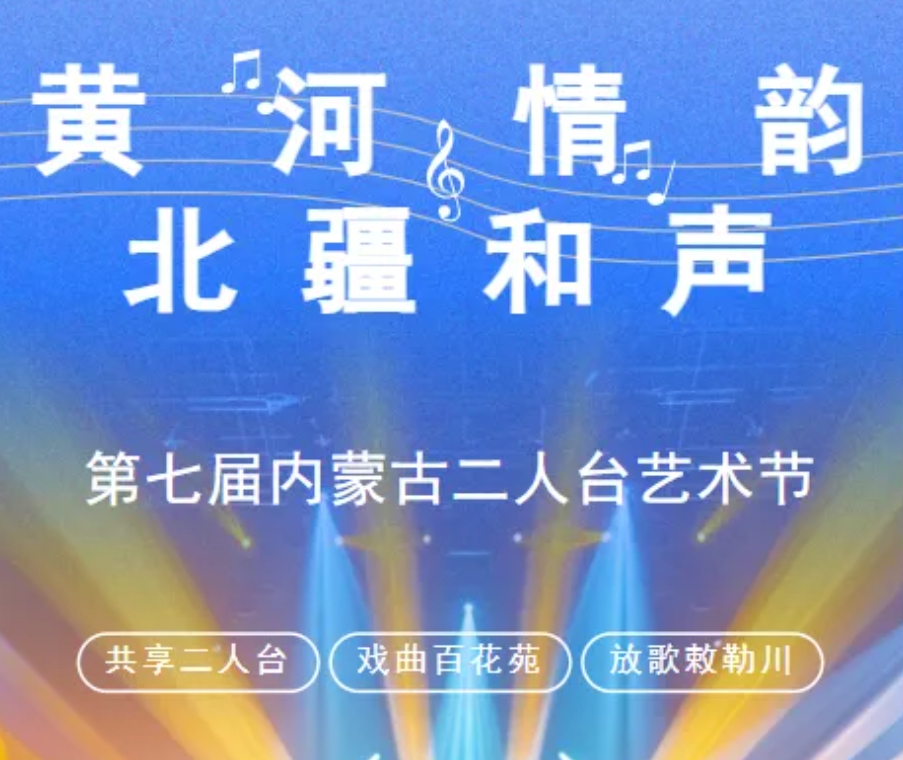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