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碧玉簪》微戏评
时间:2025-04-28 09:42:04 阅读: 次 作者:上大戏剧戏曲学
编者按
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组织之下,师生共同前往上海群众艺术馆,观看由河南省豫剧二团带来的豫剧阎派经典剧目《碧玉簪》。
《碧玉簪》讲述了大家闺秀李秀英新婚之夜因遭人陷害,被丈夫误解羞辱,却依然恪守礼教的故事。剧中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夫妻间的情感纠葛,又有家庭伦理的矛盾冲突,通过生动的剧情展现出传统女性坚韧隐忍的品格。本次演出的版本是在豫剧阎派艺术创始人阎立品先生演出本基础上进行的改编,完整地保留了阎立品先生“三盖衣”的经典表演,也对一些场次和内容进行了适当改编。 演出当晚,河南省豫剧二团的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将阎派艺术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细腻的唱腔、精准的身段和饱含情感的演绎,让剧中人物跃然舞台之上。尤其是主人公李秀英的扮演者张亚鸽,通过婉转的唱腔和传神的眼神,将角色在误解与委屈中的复杂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演出当晚,河南省豫剧二团的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将阎派艺术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细腻的唱腔、精准的身段和饱含情感的演绎,让剧中人物跃然舞台之上。尤其是主人公李秀英的扮演者张亚鸽,通过婉转的唱腔和传神的眼神,将角色在误解与委屈中的复杂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观剧完毕,师生们有感而发,撰写微戏评,萃集于本期公众号。
杨志永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后
一只玉簪和一封伪造的书信,让多疑的王玉林对新婚妻子产生嫌隙,以至于在日后的相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傲慢与偏见。到“辨簪”解开误会之前,秀英并没有得到夫婿的信任。结尾王玉林高中状元,以凤冠相送,表面上消解了与秀英之间的矛盾,实则回避了二人情感的真实修复。
“归宁”一场戏处理得最为符合人物的情感逻辑,秀英新婚满月之后回门,正当与母亲久别重逢、倾诉别离之苦时,王玉林的书信送到,要求她不能在家中留宿,须当天随轿回转。此时秀英在母亲与夫婿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即使在母亲的一再央求之下,依旧选择了当天出发。离家之时,三次回头,配合着鼓点,音乐,与大开大合的身段表演,把人物的不舍、矛盾与决绝充分体现了出来。此后的 “三盖衣”和“送冠”也是经典场次,但从剧中人物的情感立足点来看,后两场戏缺少主体情感的自我展现。“三盖衣”的三次盖衣动作并不是基于夫妻二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实则为“出嫁从夫”道德观念约束之下做出的行为。王玉林在椅子上和衣而睡,秀英想到了母亲的教导以及婆婆平日对自己的关心,继而为其盖上衣服。天明之后,这一行为却受到了王玉林的责怪与嘲讽。实际在新婚以后,二人并不存在真正的交流,三盖衣的动机本质上源于一种礼仪约束。最后一场戏,王玉林在送冠之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态度,对于此前造成的误解表示自责,在这种谦卑的美德之下,秀英的宽容被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表现。
《碧玉簪》是豫剧阎派剧目,应该说,在一定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之下,演员有着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希望在舞台上塑造出淳良、柔情、符合大多数人期望的形象。这种形象虽然是美好的,也是单一的,在此情况之下,剧中人物的自我情感为了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就进入到一种被遮蔽的真空状态。如此,公共情绪代替自己本身的价值判断,其主动选择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小。当个人情感的进退失据成为常态之后,即使发出了勇敢的悲鸣,也能够被一纸滑稽的保证书轻松瓦解。此时,大团圆结局的强大力量依旧存在。以王玉林高中状元并送给妻子凤冠来强行弥合矛盾,同样是以权力机制来代替个人判断,两人看似修得正果,实则只是形式上的接纳。若是个人的情感逻辑不再处于依存地位,而是直面信任的裂痕,可能会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引人入胜的局面。
陈章涌
24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
张亚鸽在豫剧《碧玉簪》中的表演展现出扎实功底与艺术水准。她所塑造的李秀英一角,以细腻的唱腔配合精准的身段动作,将一位饱受委屈却始终坚守尊严的女性形象诠释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特别是在秀英前期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的这一关键场次中,张亚鸽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与眼神表达,生动呈现出角色在孝顺父母与维系夫妻关系之间的复杂心境与艰难抉择,使观众可以深切感受到角色的内心波澜,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碧玉簪》的故事结尾却引发了诸多争议。当李秀英在受尽屈辱与委屈后,自我意识已然觉醒,却依然选择与那个“傻男主”冰释前嫌、回归家庭,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与此前所营造的情感基调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故事逻辑和情节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事实上,类似的情节在传统戏曲故事中并不鲜见,如《双轿接亲》《白兔记》等剧目,都存在女主在遭受严重伤害后,最终仍回归家庭的情节设定,这也普遍引发了现代观众的不适感。一方面,女主所承受的误会与伤害已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即便安排了“男主追,女主拒绝”的反转情节,也难以消解观众心中对女主所受不公的愤恨;另一方面,男主形象在剧中的刻画过于单薄,缺乏足够的魅力与优点,这也导致了女主最终回归家庭的选择很难得到现代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所以这样的结局安排,就难免让观众感到遗憾与不满。
尽管《碧玉簪》的故事结尾存在争议,但张亚鸽老师的精湛表演却成功征服了现场观众。在演出过程中,叫好声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息。她用卓越的演技,将李秀英的形象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让大家沉浸于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这也彰显了戏曲舞台从古至今令人着迷的魔力——即便故事有瑕疵,演员们仍能用精彩的表演,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艺术的无限风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
赵靖童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豫剧《碧玉簪》主要讲述了明朝吏部尚书李廷甫将女儿李秀英许婚翰林王裕之子王玉林,但李秀英的表兄顾文友因求婚被拒,暗中勾结孙媒婆,盗取李秀英的玉簪并伪造情书,于新婚之夜将证物藏入新房意图污其名节。王玉林发现后误信妻子不贞,对其冷落虐待。李廷甫听闻此事后亲审此案为女做主,虽揭露了顾文友与孙媒婆的阴谋,但李秀英已因受折磨病重多时。王玉林悔恨交加,赴京考取功名后携凤冠霞帔请罪,最终夫妻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从整个故事的框架上来看,豫剧《碧玉簪》删除了原版剧情中冗长的情节,一开场就是“拜堂”一场,将男女双方的矛盾点集中起来展现在观众面前,加快了叙事节奏,将观众带入到故事发展中。
在夫妻关系的叙述之下,“归宁”一场中李秀英与母亲的情感交流更加丰富了李秀英的人物形象。在这一场李秀英的身份从妻子变成了女儿,面对自己亲生母亲的关心却选择了“报喜不报忧”,而母亲对女儿的细心关怀更是与王玉林对李秀英冷落的态度形成了对比,表现了李秀英想留却不能留,内心深处的不断挣扎。
从主题上来看,最后王玉林考取功名与贤妻重修旧好。这是一个偏向“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但这样的结尾是否弱化了整个故事中对李秀英身心上的伤害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王玉林通过科举功名实现“赎罪”,实质是以社会地位的提升来掩盖曾经的过错,李秀英的原谅成为证明丈夫“浪子回头”的工具,而她曾被冷落虐待的身心创伤则被“中魁荣归”的荣耀轻巧覆盖。古典戏曲中“团圆”的结局承载着百姓对和谐秩序的愿望,在当下时代的改编中我们也可将其转化为反思的起点,尽管“凤冠霞帔”的团圆结局仍难逃封建伦理的惯性叙事,但李秀英“不要凤冠要信任”的宣言,已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安宁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百年前,彼时尚未更名“越剧”的男班艺人们为了在当时繁华的上海站稳脚跟,改编形成了《碧玉簪》一剧,于上海首演后大受欢迎,而后《碧玉簪》也成为了越剧各剧团、流派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这个春天,河南豫剧院二团携阎派经典《碧玉簪》南下上海,在这个越剧盛行的城市演绎了一出充满中原气韵的情感大戏。作为曾观看过越剧版《碧玉簪》的观众,此次观剧体验犹如在熟悉的故事框架中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豫剧的豪迈与越剧的婉约在同一个故事蓝本上碰撞交锋,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也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首先,此次改编显然是豫剧在经典故事框架中凸显地域特色的优秀案例。《碧玉簪》的核心故事围绕明代闺阁女子李秀英的婚姻悲剧展开,因碧玉簪误会引发的夫妻隔阂、家庭矛盾,最终以“三盖衣”等经典段落完成情感递进,直至真相大白的大团圆结局。这一题材在越剧、婺剧等多个剧种中均有演绎,而豫剧版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唱词还是念白均做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改编,例如相较于越剧版偏向文人化的台词设计,豫剧版的念白与唱词更显质朴泼辣,以河南方言特有的声调韵律,将北方女子的性格特征展现得当。
同时,张亚鸽饰演的李秀英,无疑是当晚演出的一大亮点。作为阎派传人,她的唱腔兼具细腻婉转与刚劲有力,体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让李秀英的形象突破了传统戏曲中“贤妻”的单一标签,呈现出更为立体的情感层次。
本次豫剧《碧玉簪》在上海的演出无疑是一次地方戏跨地域传播的有力尝试。一方面,剧团坚守阎派艺术的精髓,从唱腔板式到身段规范都严格遵循传统,让上海观众得以领略原汁原味的豫剧魅力;另一方面,在舞美、音乐等方面的适度创新,又让相对传统的地方戏在当代剧场中焕发新生。然而,这种传播也面临着现实挑战:如何在保留剧种特色的同时,让剧情逻辑更符合现代价值观?例如,剧中王玉林在得知真相后的“送凤冠”情节,豫剧版延续了传统戏曲中“夫为妻纲”的伦理框架,王玉林的悔悟更多停留在“知错能改”的层面,而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伤害缺乏更深层的反思。在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视角中,这种传统处理方式虽保留了历史真实感,却也可能引发其对剧情价值观的争议。
这场演出或许不是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戏曲传承的真实状态:它需要坚守,也需要反思;需要传统,也需要新潮。愿河南豫剧院二团今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舞台作品。
任思琦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作为越剧四大经典剧目之一的《碧玉簪》,其渊源可追溯至民间艺人马潮水根据《李秀英宝卷》和东阳班《三家绝》改编的早期版本。这部历经百年传承的婚恋题材剧作,在阎派创始人阎立品移植为豫剧版本后,经王明山、张凌羽改编、河南豫剧院二团精心打磨,重新搬上舞台。
《碧玉簪》的核心情节是:尚书之女李秀英与翰林之子王玉林喜结连理前夕,秀英的表兄顾文友因求婚遭拒,竟勾结孙媒婆窃取秀英的碧玉发簪,并伪造情书藏于婚房之中。王玉林洞房花烛夜发现蹊跷后,认定李秀英行为不检,自此对她百般冷落、言语羞辱,甚至萌生休妻之念。待真相大白后,李秀英对丈夫的猜忌深感心寒,而王玉林为表悔意赴京赶考高中状元,最终身着官服手持凤冠霞帔向妻子请罪。
与原剧相比,豫剧《碧玉簪》弱化了李秀英一味忍让的被动性,强化了行动的合理性,使人物形象更符合观众期待,较好地实现了传统题材的现代转译。豫剧《碧玉簪》在保留“三盖衣”“送凤冠”等经典场次的基础上,淡化了传统伦理框架对女性自主性的规训,放大了李秀英的自尊自爱。“三盖衣”一场,是李秀英内心矛盾和复杂情绪的集中展现,虽然心有怨气,但善良贤淑的本性又让她狠不下心,内心痛楚压抑却又无处诉说。真相大白后她毅然归家,得知王玉林中状元也没有刻意逢迎,而是用“不要凤冠要信任,不要霞帔要自尊”一句,显示出坚强、独立的现代品格,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
在音乐唱腔方面,演员巧妙平衡了越剧的婉约基因与豫剧的激越特质。阎派讲究“含蓄内敛、以情带声”,主演张亚鸽音色变化丰富,声韵浓淡相宜,将新嫁娘从隐忍委屈到自我觉醒的心理嬗变,化作可听可见的情感波涛,极具感染力。再加上滚白、垛板的巧妙运用和对旋律、节奏的恰当处理,使得唱腔既有浓郁的剧种特色,又有演员的个人魅力。
此外,还加入“咱几个老人别魔怔,让他俩单独抒抒情”、“此时刻莫要再强硬,火候不到饭难成”等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念白,生动有趣,为悲剧底色注入一抹喜剧亮色。
但在观看过程中,王玉林、李廷甫殴打、辱骂李秀英的场面还是让人略感不适,略显刺目。如何在保留戏剧冲突真实性的前提下,避免对现代观众造成观感不适,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杨茗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豫剧《碧玉簪》剧情更紧凑,结构更清晰,减少了对李秀英与王玉林家庭情况的描述,转而在对话中进行简单交代,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上,这种 “去冗余化” 处理使剧情推进更显紧凑,例如在秀英看到王玉林受冷时,一方面受到冷落与莫名受气,回门当天便被叫回的愤怒让她不愿照顾王玉林,另一方面,在家中学的三从四德,母亲教的要照顾丈夫,为了避免父母被外人指点又想要为他添衣,这种来回拉扯,变扭的情绪被很准确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忍不住与李秀英共情,痛斥王玉林的不辨是非,不问缘由就单方面冷暴力。
又者,在情节架构的层面,豫剧的剧本调转了回门与披衣的桥段,这种改动相比起原剧本更能深化人物的情绪,比起原作说秀英给王玉林盖衣服是“不检点”,王玉林在试图以回门为借口休妻不成后再以披衣为借口更为符合人物行为逻辑,有效强化了人物行动的因果关系与戏剧冲突的合理性。但尽管作了诸多改编,剧本也依旧有部分“大男子主义”的封建内容,例如王玉林虽是借口想休妻但借口披女人衣服考不上功名甚至打骂李秀英,原本这种内容本应该呈现出对旧道德的批判,但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却也消解了潜在的批判力度。
在人物塑造维度,《碧玉簪》突破了传统贤妻良母式的单一角色塑造,让其中的女性角色都十分有魅力,首先主角李秀英,既“恪守礼教”,有传统的美德,又有 “自主意识”,是为自己的幸福,为家庭的幸福而考虑的成熟女性。作为尚书家的千金小姐,一方面她尊重婆婆与丈夫,尽到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脾气,绝不轻易饶过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男人,并不盲从父母的意见,而是为自己的幸福而考虑,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而丰满。秀英的丫鬟春香,活泼可爱又带着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对小姐忠心耿耿,秀英的婆婆,爱护儿媳,绝不一味地站在儿子这边,待秀英就像对待亲女儿一样爱护与亲切,同时又带了些幽默,一改一些传统剧目中的“恶婆婆”形象,秀英的母亲也是展现出了中国式亲情的复杂细腻,她不仅是非常爱护女儿的母亲形象,但也有对女儿发怒,甚至到“断绝关系”这样的嘴硬与威胁,但是她也是最关心女儿的,能第一时间发觉女儿的不开心与不对劲,敏锐捕捉到女儿情绪变化。对这些女性角色的再塑造,也更丰富了戏曲文本的层次,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排版丨安宁
审核丨赵晓红、张婷婷、廖亮、邓黛
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组织之下,师生共同前往上海群众艺术馆,观看由河南省豫剧二团带来的豫剧阎派经典剧目《碧玉簪》。
《碧玉簪》讲述了大家闺秀李秀英新婚之夜因遭人陷害,被丈夫误解羞辱,却依然恪守礼教的故事。剧中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夫妻间的情感纠葛,又有家庭伦理的矛盾冲突,通过生动的剧情展现出传统女性坚韧隐忍的品格。本次演出的版本是在豫剧阎派艺术创始人阎立品先生演出本基础上进行的改编,完整地保留了阎立品先生“三盖衣”的经典表演,也对一些场次和内容进行了适当改编。

观剧完毕,师生们有感而发,撰写微戏评,萃集于本期公众号。
杨志永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后
一只玉簪和一封伪造的书信,让多疑的王玉林对新婚妻子产生嫌隙,以至于在日后的相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傲慢与偏见。到“辨簪”解开误会之前,秀英并没有得到夫婿的信任。结尾王玉林高中状元,以凤冠相送,表面上消解了与秀英之间的矛盾,实则回避了二人情感的真实修复。
“归宁”一场戏处理得最为符合人物的情感逻辑,秀英新婚满月之后回门,正当与母亲久别重逢、倾诉别离之苦时,王玉林的书信送到,要求她不能在家中留宿,须当天随轿回转。此时秀英在母亲与夫婿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即使在母亲的一再央求之下,依旧选择了当天出发。离家之时,三次回头,配合着鼓点,音乐,与大开大合的身段表演,把人物的不舍、矛盾与决绝充分体现了出来。此后的 “三盖衣”和“送冠”也是经典场次,但从剧中人物的情感立足点来看,后两场戏缺少主体情感的自我展现。“三盖衣”的三次盖衣动作并不是基于夫妻二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实则为“出嫁从夫”道德观念约束之下做出的行为。王玉林在椅子上和衣而睡,秀英想到了母亲的教导以及婆婆平日对自己的关心,继而为其盖上衣服。天明之后,这一行为却受到了王玉林的责怪与嘲讽。实际在新婚以后,二人并不存在真正的交流,三盖衣的动机本质上源于一种礼仪约束。最后一场戏,王玉林在送冠之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态度,对于此前造成的误解表示自责,在这种谦卑的美德之下,秀英的宽容被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表现。
《碧玉簪》是豫剧阎派剧目,应该说,在一定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之下,演员有着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希望在舞台上塑造出淳良、柔情、符合大多数人期望的形象。这种形象虽然是美好的,也是单一的,在此情况之下,剧中人物的自我情感为了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就进入到一种被遮蔽的真空状态。如此,公共情绪代替自己本身的价值判断,其主动选择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小。当个人情感的进退失据成为常态之后,即使发出了勇敢的悲鸣,也能够被一纸滑稽的保证书轻松瓦解。此时,大团圆结局的强大力量依旧存在。以王玉林高中状元并送给妻子凤冠来强行弥合矛盾,同样是以权力机制来代替个人判断,两人看似修得正果,实则只是形式上的接纳。若是个人的情感逻辑不再处于依存地位,而是直面信任的裂痕,可能会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引人入胜的局面。

陈章涌
24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
张亚鸽在豫剧《碧玉簪》中的表演展现出扎实功底与艺术水准。她所塑造的李秀英一角,以细腻的唱腔配合精准的身段动作,将一位饱受委屈却始终坚守尊严的女性形象诠释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特别是在秀英前期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的这一关键场次中,张亚鸽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与眼神表达,生动呈现出角色在孝顺父母与维系夫妻关系之间的复杂心境与艰难抉择,使观众可以深切感受到角色的内心波澜,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碧玉簪》的故事结尾却引发了诸多争议。当李秀英在受尽屈辱与委屈后,自我意识已然觉醒,却依然选择与那个“傻男主”冰释前嫌、回归家庭,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与此前所营造的情感基调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故事逻辑和情节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事实上,类似的情节在传统戏曲故事中并不鲜见,如《双轿接亲》《白兔记》等剧目,都存在女主在遭受严重伤害后,最终仍回归家庭的情节设定,这也普遍引发了现代观众的不适感。一方面,女主所承受的误会与伤害已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即便安排了“男主追,女主拒绝”的反转情节,也难以消解观众心中对女主所受不公的愤恨;另一方面,男主形象在剧中的刻画过于单薄,缺乏足够的魅力与优点,这也导致了女主最终回归家庭的选择很难得到现代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所以这样的结局安排,就难免让观众感到遗憾与不满。
尽管《碧玉簪》的故事结尾存在争议,但张亚鸽老师的精湛表演却成功征服了现场观众。在演出过程中,叫好声此起彼伏,掌声经久不息。她用卓越的演技,将李秀英的形象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让大家沉浸于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这也彰显了戏曲舞台从古至今令人着迷的魔力——即便故事有瑕疵,演员们仍能用精彩的表演,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艺术的无限风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
赵靖童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豫剧《碧玉簪》主要讲述了明朝吏部尚书李廷甫将女儿李秀英许婚翰林王裕之子王玉林,但李秀英的表兄顾文友因求婚被拒,暗中勾结孙媒婆,盗取李秀英的玉簪并伪造情书,于新婚之夜将证物藏入新房意图污其名节。王玉林发现后误信妻子不贞,对其冷落虐待。李廷甫听闻此事后亲审此案为女做主,虽揭露了顾文友与孙媒婆的阴谋,但李秀英已因受折磨病重多时。王玉林悔恨交加,赴京考取功名后携凤冠霞帔请罪,最终夫妻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从整个故事的框架上来看,豫剧《碧玉簪》删除了原版剧情中冗长的情节,一开场就是“拜堂”一场,将男女双方的矛盾点集中起来展现在观众面前,加快了叙事节奏,将观众带入到故事发展中。
在夫妻关系的叙述之下,“归宁”一场中李秀英与母亲的情感交流更加丰富了李秀英的人物形象。在这一场李秀英的身份从妻子变成了女儿,面对自己亲生母亲的关心却选择了“报喜不报忧”,而母亲对女儿的细心关怀更是与王玉林对李秀英冷落的态度形成了对比,表现了李秀英想留却不能留,内心深处的不断挣扎。
从主题上来看,最后王玉林考取功名与贤妻重修旧好。这是一个偏向“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但这样的结尾是否弱化了整个故事中对李秀英身心上的伤害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王玉林通过科举功名实现“赎罪”,实质是以社会地位的提升来掩盖曾经的过错,李秀英的原谅成为证明丈夫“浪子回头”的工具,而她曾被冷落虐待的身心创伤则被“中魁荣归”的荣耀轻巧覆盖。古典戏曲中“团圆”的结局承载着百姓对和谐秩序的愿望,在当下时代的改编中我们也可将其转化为反思的起点,尽管“凤冠霞帔”的团圆结局仍难逃封建伦理的惯性叙事,但李秀英“不要凤冠要信任”的宣言,已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安宁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百年前,彼时尚未更名“越剧”的男班艺人们为了在当时繁华的上海站稳脚跟,改编形成了《碧玉簪》一剧,于上海首演后大受欢迎,而后《碧玉簪》也成为了越剧各剧团、流派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这个春天,河南豫剧院二团携阎派经典《碧玉簪》南下上海,在这个越剧盛行的城市演绎了一出充满中原气韵的情感大戏。作为曾观看过越剧版《碧玉簪》的观众,此次观剧体验犹如在熟悉的故事框架中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豫剧的豪迈与越剧的婉约在同一个故事蓝本上碰撞交锋,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也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首先,此次改编显然是豫剧在经典故事框架中凸显地域特色的优秀案例。《碧玉簪》的核心故事围绕明代闺阁女子李秀英的婚姻悲剧展开,因碧玉簪误会引发的夫妻隔阂、家庭矛盾,最终以“三盖衣”等经典段落完成情感递进,直至真相大白的大团圆结局。这一题材在越剧、婺剧等多个剧种中均有演绎,而豫剧版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唱词还是念白均做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改编,例如相较于越剧版偏向文人化的台词设计,豫剧版的念白与唱词更显质朴泼辣,以河南方言特有的声调韵律,将北方女子的性格特征展现得当。
同时,张亚鸽饰演的李秀英,无疑是当晚演出的一大亮点。作为阎派传人,她的唱腔兼具细腻婉转与刚劲有力,体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让李秀英的形象突破了传统戏曲中“贤妻”的单一标签,呈现出更为立体的情感层次。
本次豫剧《碧玉簪》在上海的演出无疑是一次地方戏跨地域传播的有力尝试。一方面,剧团坚守阎派艺术的精髓,从唱腔板式到身段规范都严格遵循传统,让上海观众得以领略原汁原味的豫剧魅力;另一方面,在舞美、音乐等方面的适度创新,又让相对传统的地方戏在当代剧场中焕发新生。然而,这种传播也面临着现实挑战:如何在保留剧种特色的同时,让剧情逻辑更符合现代价值观?例如,剧中王玉林在得知真相后的“送凤冠”情节,豫剧版延续了传统戏曲中“夫为妻纲”的伦理框架,王玉林的悔悟更多停留在“知错能改”的层面,而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伤害缺乏更深层的反思。在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视角中,这种传统处理方式虽保留了历史真实感,却也可能引发其对剧情价值观的争议。
这场演出或许不是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戏曲传承的真实状态:它需要坚守,也需要反思;需要传统,也需要新潮。愿河南豫剧院二团今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舞台作品。

任思琦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作为越剧四大经典剧目之一的《碧玉簪》,其渊源可追溯至民间艺人马潮水根据《李秀英宝卷》和东阳班《三家绝》改编的早期版本。这部历经百年传承的婚恋题材剧作,在阎派创始人阎立品移植为豫剧版本后,经王明山、张凌羽改编、河南豫剧院二团精心打磨,重新搬上舞台。
《碧玉簪》的核心情节是:尚书之女李秀英与翰林之子王玉林喜结连理前夕,秀英的表兄顾文友因求婚遭拒,竟勾结孙媒婆窃取秀英的碧玉发簪,并伪造情书藏于婚房之中。王玉林洞房花烛夜发现蹊跷后,认定李秀英行为不检,自此对她百般冷落、言语羞辱,甚至萌生休妻之念。待真相大白后,李秀英对丈夫的猜忌深感心寒,而王玉林为表悔意赴京赶考高中状元,最终身着官服手持凤冠霞帔向妻子请罪。
与原剧相比,豫剧《碧玉簪》弱化了李秀英一味忍让的被动性,强化了行动的合理性,使人物形象更符合观众期待,较好地实现了传统题材的现代转译。豫剧《碧玉簪》在保留“三盖衣”“送凤冠”等经典场次的基础上,淡化了传统伦理框架对女性自主性的规训,放大了李秀英的自尊自爱。“三盖衣”一场,是李秀英内心矛盾和复杂情绪的集中展现,虽然心有怨气,但善良贤淑的本性又让她狠不下心,内心痛楚压抑却又无处诉说。真相大白后她毅然归家,得知王玉林中状元也没有刻意逢迎,而是用“不要凤冠要信任,不要霞帔要自尊”一句,显示出坚强、独立的现代品格,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
在音乐唱腔方面,演员巧妙平衡了越剧的婉约基因与豫剧的激越特质。阎派讲究“含蓄内敛、以情带声”,主演张亚鸽音色变化丰富,声韵浓淡相宜,将新嫁娘从隐忍委屈到自我觉醒的心理嬗变,化作可听可见的情感波涛,极具感染力。再加上滚白、垛板的巧妙运用和对旋律、节奏的恰当处理,使得唱腔既有浓郁的剧种特色,又有演员的个人魅力。
此外,还加入“咱几个老人别魔怔,让他俩单独抒抒情”、“此时刻莫要再强硬,火候不到饭难成”等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念白,生动有趣,为悲剧底色注入一抹喜剧亮色。
但在观看过程中,王玉林、李廷甫殴打、辱骂李秀英的场面还是让人略感不适,略显刺目。如何在保留戏剧冲突真实性的前提下,避免对现代观众造成观感不适,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杨茗
23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
豫剧《碧玉簪》剧情更紧凑,结构更清晰,减少了对李秀英与王玉林家庭情况的描述,转而在对话中进行简单交代,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上,这种 “去冗余化” 处理使剧情推进更显紧凑,例如在秀英看到王玉林受冷时,一方面受到冷落与莫名受气,回门当天便被叫回的愤怒让她不愿照顾王玉林,另一方面,在家中学的三从四德,母亲教的要照顾丈夫,为了避免父母被外人指点又想要为他添衣,这种来回拉扯,变扭的情绪被很准确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忍不住与李秀英共情,痛斥王玉林的不辨是非,不问缘由就单方面冷暴力。
又者,在情节架构的层面,豫剧的剧本调转了回门与披衣的桥段,这种改动相比起原剧本更能深化人物的情绪,比起原作说秀英给王玉林盖衣服是“不检点”,王玉林在试图以回门为借口休妻不成后再以披衣为借口更为符合人物行为逻辑,有效强化了人物行动的因果关系与戏剧冲突的合理性。但尽管作了诸多改编,剧本也依旧有部分“大男子主义”的封建内容,例如王玉林虽是借口想休妻但借口披女人衣服考不上功名甚至打骂李秀英,原本这种内容本应该呈现出对旧道德的批判,但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却也消解了潜在的批判力度。
在人物塑造维度,《碧玉簪》突破了传统贤妻良母式的单一角色塑造,让其中的女性角色都十分有魅力,首先主角李秀英,既“恪守礼教”,有传统的美德,又有 “自主意识”,是为自己的幸福,为家庭的幸福而考虑的成熟女性。作为尚书家的千金小姐,一方面她尊重婆婆与丈夫,尽到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脾气,绝不轻易饶过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男人,并不盲从父母的意见,而是为自己的幸福而考虑,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而丰满。秀英的丫鬟春香,活泼可爱又带着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对小姐忠心耿耿,秀英的婆婆,爱护儿媳,绝不一味地站在儿子这边,待秀英就像对待亲女儿一样爱护与亲切,同时又带了些幽默,一改一些传统剧目中的“恶婆婆”形象,秀英的母亲也是展现出了中国式亲情的复杂细腻,她不仅是非常爱护女儿的母亲形象,但也有对女儿发怒,甚至到“断绝关系”这样的嘴硬与威胁,但是她也是最关心女儿的,能第一时间发觉女儿的不开心与不对劲,敏锐捕捉到女儿情绪变化。对这些女性角色的再塑造,也更丰富了戏曲文本的层次,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排版丨安宁
审核丨赵晓红、张婷婷、廖亮、邓黛
猜你喜欢
豫剧碧玉簪简介,该剧目讲述明朝吏部尚书李廷甫将女儿秀英许配翰林王裕之子玉林。...
豫剧优秀传统戏《风雨情缘》,在《大祭桩》的基础上进行升华、改编,唱词更具文学性,精湛的表演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赞可。...
豫剧《太行之子》以“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这一真实人物为原型,生动地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时光回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彼时的太行山区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豫剧碧玉簪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当代女性心声的表达。 本届展演一如既往地坚持低票价、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1月1日,郑州大剧院四周年演出季开幕,河南豫剧二团演出的豫剧阎派经典剧目《碧玉簪》《秦雪梅》先后在郑州大剧院戏曲厅与广大观众见面。据郑州大剧院统计,演出开始前一周,两场演出票均被抢购,许多观众不得不抱憾等待。...
9月25日晚,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豫剧院承办,河南豫剧二团演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文艺活动——2024年河南省艺术点亮演出季公益惠民演出活动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成功举办;...
9月22日晚,河南豫剧三团携经典保留剧目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在昆山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受邀参加“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人员优秀剧目邀请展演”,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看,现场掌声如潮,气氛热烈。...
豫剧《包青天》,又名《秦香莲》《铡美案》,崔派“四大悲剧”之一。讲述宋代秦香莲之夫陈世美进京应试三年未归,家乡荒旱公婆饿死,秦香莲无奈携儿女赴汴梁寻夫,始知陈世美得中状元招为附马。...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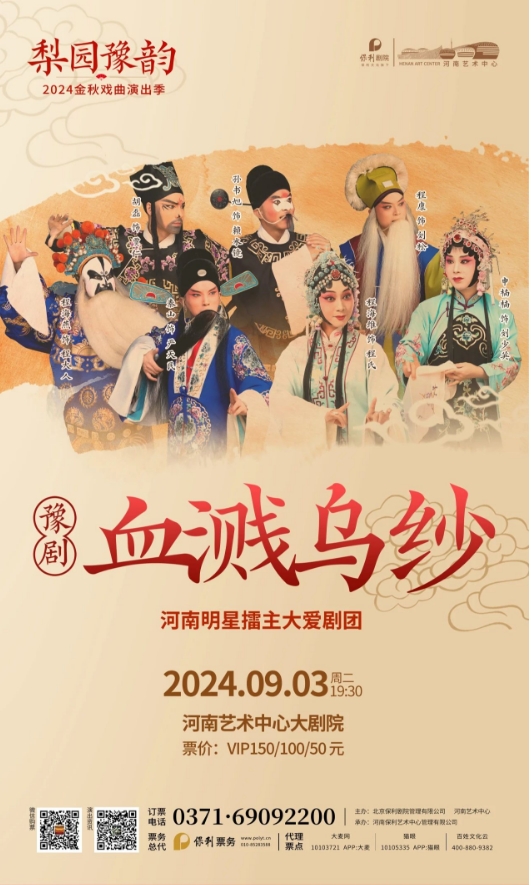
评论列表